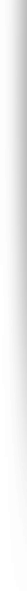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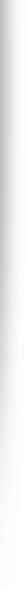
|
禅宗的解释学
作者:朱彩方 索菲亚大学 中文翻译:刘璘 索菲亚大学
原文出处: Asian Philosophy Vol. 21, No. 4, November 2011, pp. 375–393 |
(注:完整篇幅分为2次发布,剩余部分请关注下篇文章)
禅宗解释学:从〈碧岩录〉阅读公案(1)
朱彩方
摘要
尽管禅宗——尤其是公案禅——在实践形态上高度非常规且令人困惑,但仍然存在若干原则,可据以理解与欣赏其修行实践。禅宗的五家(或五宗)各自具有独特的解释学规则:例如,临济宗有临济四料简、四宾主与四照用等原则;而云门宗则以云门三句作为其宗门规范之一。此外,还存在一套跨宗派适用的总体性内在逻辑,似乎能够用来理解不同禅宗传统中的相遇对话。在恰当机缘(禅机)中迅捷而善巧地回应,同时又始终安住于心之开放与流动之中,这一能力凸显了禅宗行者在认知与行为层面的内在逻辑。本文尝试在禅宗解释学的视域下,重读《碧岩录》中的公案。禅宗相遇中的某些层面与运作模式,或可呈现为仪式性形态:它们既可能作为面向大众的权宜方便,也可能作为觉悟行为的体现。然而,对禅宗生活的程式化仪式化,却与禅宗生活方式所蕴含的自由与自发精神背道而驰。在我们最终诉诸于那种超个人层面的“高贵的沉默”之前,关于被神秘化的公案禅经验,仍有大量内容可以、也亟需得到阐明。
一、引言
禅宗,尤其是公案禅¹,主张通过非语言的表达方式,直接体现本心——这一心态在心理学中通常被描述为心灵的“改变状态”(altered states)或“替代状态”(alternate states)。当这一原初心态得以体现时,行者便能见心之性,从而成佛。公案禅在实践中对非语言表达的高度运用,使其既令人困惑,又充满创造性与吸引力。“公案”作为禅宗参究中的一种公开检验案例,通常通过相遇式对话展开;然而,它常被一些人简单地翻译为一种禅宗谜语。在过去大约五十年的时间里,从制度、社会、历史、文学、语文学以及神学/哲学等路径出发,对禅宗所展开的学术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然而,几乎尚未有研究真正运用个案研究与第一手文献,来细致审视公案禅经验的“内在逻辑”。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尝试探究并梳理禅宗在认知与行为层面上的内在逻辑,从而使那些晦涩难解的公案,尽可能为当代的一般读者所理解。这一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始终与本来心态保持连通,并从这一心态出发,展开自发而善巧的行动。在我们最终诉诸于所谓的“高贵的沉默”,或其他任何非语言的具现形式之前,关于这一问题,仍有大量内容可以、也亟需得到澄清。本文所采用的澄清与诠释方法,是一种融入心理学视角的佛教解释学,同时也借鉴了部分现代西方解释学的理论资源。无论是对禅宗的研究,还是对宗教研究这一领域的整体发展而言,这一路径都有助于更为清晰地揭示人类认知、决断、沟通与互动方式中那种难以捉摸的运作机制。本文亦期望,这种研究取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学术研究者与修行实践者之间的“局内人—局外人”鸿沟;这一鸿沟长期以来分隔着佛教研究中的学术共同体与实践共同体(McRae,2003;Zhu,2009)。
本文所分析的公案样本,选自《碧岩录》。这是一部在公案研究中具有典范地位的经典文献。本论文的第二与第三节,分别在禅宗的宏观脉络中,介绍《碧岩录》的基本特征,以及公案禅的总体面貌。第四节探讨佛教解释学的一般原则,例如方便(upāya)或权宜手段。第五节则较为深入地展示了如何在禅宗解释学的视角下阅读与理解公案的具体实践。尽管论文中涉及不少临济宗,但篇幅上更多着力于云门宗的风格,以及禅机——即禅宗相遇中“当下转变的契机”——的运作与应用。对现代西方解释学的相关讨论,将主要出现在第四与第五节中。第六节则简要讨论禅宗、仪式与仪式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认为,作为《碧岩录》的作者,圆悟通过其大量而深入的评唱与阐释,对原本过于晦涩、令人困惑且常被误解的公案禅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贡献。正是这些评唱,为其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公案注释奠定了基础。尽管传统注释往往较少关注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以及文学体裁与作者身份的一致性问题,但它们在传心灯这一过程的心理层面(尤其是超个人心理学意义上的)与灵性层面所投注的关注,却呈现出相当的一致性。因此,这些注释为我们当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使我们得以汲取养分,继续推进对公案仍相对未知的内在逻辑的梳理与阐明。得益于圆悟禅师奠基性的工作,以及现代心理学工具的引入,去神秘化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可行性,也更为人所期待。
本体论唯有通过现象学方得以成立,而现象学则只能通过解释来加以阐明。尽管《碧岩录》曾被大慧宗杲——圆悟的弟子——付之一炬,但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从当下对话语禅(Discourse Chan)复兴的现实需要来看,这一取向都与佛教关于善巧运用、权宜手段的教导高度契合:即运用后得智(pṛṣṭha-labdha-jñāna)——在觉悟之后随即获得的继起之智——来促成对佛法的理解与欣赏。在禅宗相遇中,单纯的沉默或非语言表达,既可能是觉悟的具现,也可能只是木讷与失语。正是对后得智的有效运用,而非停留于根本智(mūla-jñāna)——那种源自无分别的本体经验的根本智慧——使得佛陀得以以其长广舌,为一切众生阐说佛法、利益群生。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禅宗学者或兼具修行身份的研究者,是否可以、也是否应当以一条“广长舌”,来言说与阐明公案经验中那细微而隐秘的内在逻辑?这一言说,或可被理解为 Paul Ricoeur(1981)所称的“第二次天真”,以及 Ken Wilber(1986)所称的超个人意识之经验表达。
二、《碧岩录》
The BlueCliffRecord是为其中文书名《碧岩录》(Biyanlu)的英语直译,由宋代(公元960–1260年)禅宗大师圆悟克勤(1063–1135)编纂而成。该书常被尊奉为禅宗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甚至被誉为“第一等书”(麻天祥,1997,第91页)²。全书收录了来自禅宗五家(亦即五大支系)的100则公案:沩仰、临济(日:Rinzai)、曹洞(日:Sōtō)、云门(日:Ummon)与法眼。《碧岩录》中每一则公案单元通常由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在这100则中,有80则以圆悟的一段简短提示开篇,英文译者Thomas Cleary与J.C.Cleary将其称为 “垂示”(pointer),其作用在于引导读者进入公案情境,并点出所引公案的哲学或心理意涵。
对于这 80 则带有提示的公案,其第二个组成部分恒为“古则”——字面义为“古代案例”,亦即狭义上的公案本身。古则通常篇幅极为简短,但在语文学、哲学以及心理—灵性层面均极具挑战性。第三个部分是“评唱”,即禅师圆悟所作的注解³。此一注解往往篇幅较长,通过将公案置入多重语境之中,提出圆悟个人的挑战性解读(内释/自释,isogesis),并给出其禅宗分析与解释的指引(释经,exegesis)。在某些情况下,外在的释经与内在的自释之间并不容易区分;而这一部分,通常正是深入理解公案的关键所在。
第四个部分是“颂古”,即禅师雪窦(日:Setchō,980–1052)为该公案所作的赞颂偈。其将诗性之优雅与禅的直觉巧妙融合,使这些偈颂成为杰作;正如有学者所言,唯有“同时具备中国诗学与禅学必要知识的真正诗人”,才能给予它们应有的关注(Sekida & Grimstone,2005,第 20 页)。
每一则公案单元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圆悟对雪窦颂古所作的再度评唱与注解(CBETA,2009a)。
在对公案文献所作的形式与结构研究中,T. Griffith Foulk(2000)恰当地指出,公案文本中存在着多重声音;并将雪窦对古则所作的颂古视为第一层注释,而将圆悟所作的散文评唱——兼具释经(exegesis)与内释/自释(isogesis)——界定为第二层注释。Foulk(2000)还通过对《碧岩录》公案结构的文献分析,论证了其中所呈现的社会动力结构(例如师徒之间、裁判者与被裁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所体现的仪式化表演特征。我们可以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 Foulk 对其所谓禅宗文献中“对话体裁的惯例”的判断,即:师者之声……始终代表着觉悟的立场(Foulk,2000,第 33 页)。然而,我们却难以同意他进一步主张的观点,即认为对话中的回应者或弟子之声“始终处于劣位”,并且必然是迷妄的(2000,第 33 页)。这种非黑即白式的分析二分法,在禅宗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反例。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显然无法解释临济宗所提出的“临济四宾主”之中至少两种师徒关系类型;而这一问题,我们将于本文第五节(禅宗解释学)中作进一步讨论。
圆悟在《碧岩录》中所作的大量评唱与释解构成了全书的主体内容,并标志着话语禅的成熟;这一形态在历史上出现在宋代公案禅走向式微之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话语禅究竟是一种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发展性回应,还是仅仅作为对表面上令人困惑的公案禅所形成的一种偶然性的对立形态?
三、公案禅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尽管几乎所有宗教最终都会指向某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存在状态,但或许唯有禅宗,将通过非语言的表达与行为来呈现不可言说者这一努力,推至极限。在诸多禅宗形态之中,公案禅无疑在这种尝试上最为富于创造性且最具戏剧性。从时间脉络上看,中国禅宗各主要形态的发展,大致横跨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这些形态通常包括:祖师禅、公案禅、话语禅(也称文字禅)、默照、看话禅(也称话头禅)以及念佛禅(一种融合禅宗与净土宗的双修实践)。
祖师禅通常被认为起源于菩提达摩于四世纪自印度或中亚来到中国之时。相传,菩提达摩将内在光明的传心仅传与一位继承者⁵(Broughton,1999;Faure,1991;印顺,1992),其后继者亦依此方式相传,直至第六代。关于六祖,学界与传统说法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是慧能(日:Eno,638–713)。中国佛教传统上将《坛经》归属于慧能,并视其为禅宗的核心定教典籍(CBETA,2009c,2009d;Faure,1991,1993;净慧,1997;马祖,1997;McRae,2000;Robinson,1997;印顺,1992)。祖师禅的风格朴素而简要:修行者多从事正式的坐禅修习,而较少——甚至几乎不——使用高度晦涩、令人困惑的语言,无论是语言性的还是非语言性的;这与公案禅所呈现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相传,作为禅宗顿悟派的奠基者,慧能将心印的传承传与多位弟子。
在慧能打破了单一继承者传承的模式之后,公案禅开始发展并逐渐兴盛。在《坛经》中,慧能对坐禅(日:zazen,字面义为“修习坐姿禅定”)的定义作出了具有革命性的重新界定:
“不于一切外境上起念,即名为坐;见自本性不动,即名为禅。”
——《坛经》(CBETA,2009c)
循此新定义而行,人们开始淡化,甚至在某些情境中完全放弃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坐禅实践。正如一则著名的譬喻所言:
“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引自相关传统表述(Faure,1993)。
怀让,慧能的三位主要法嗣之一,曾对马祖提出挑战;而马祖作为怀让的法嗣,后来成为洪州宗的奠基者,并因其“心即是佛”、“平常心是道”等教说而成为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自此之后,禅宗修行者逐渐形成一种风尚:通过参究公案并参与禅宗相遇式对话(“机锋对答”)而求得觉悟。
Mario Poceski(2007)试图正名宋代文人及编纂者在书写中所操纵、并加以强化的洪州禅的过度激进化形象。尽管如此,他仍然指出,洪州禅一方面在教义与解脱论结构上延续了早期禅宗与大乘佛教的思想脉络,另一方面又“将这些传统要素与新的概念并置”,从而“以其自身传统所特有的方式对其加以重新配置与表达”(2007,第 158 页)。因此,我们可以推定,“以心传心、以灯传灯”的传承并未中断,但其表达方式开始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
Koan是汉语“公案”(gongan)一词的日语音译,指的是一种禅宗案例,其中展开的是高度象征性、带有隐秘意味的机锋对话或互动交流,通常发生在禅宗学人与禅师之间。有时,它也仅仅表现为禅师提出的一句陈述或一个供参究的问题。师徒之间的互动一般迅速而简短,其意义往往更多体现在非语言层面,而不是语言表述本身。从传统意义上看,冗长而对话式的交流被认为类似于“葛藤”(trailing vines),这种方式违背了直指人心的原则,因此应当谨慎避免。在公案禅中,尽管在某些公案情境里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仪式化问答,但总体而言,一切可设想的表达方式都可以被运用,用以检验、确认或触发对人类心之本性的觉悟——这一心性被理解为一种无限开放、无分别的超个人意识状态。正是在这里,公案禅那种“非逻辑却具有内在逻辑”的话语形态得以展开,并最终回归其源头。公案禅文献这一体裁“规定了其主题永远不会改变:在这一语境中,禅师所说或所做的一切,始终都指向觉悟本身”(Foulk, 2000,第39–40 页)。禅师被认为在言说与行动的过程中,从未离开这种超个人或替代性的意识状态;正是这一状态,使得师徒之间的相遇得以自发而善巧地展开。与唯识佛教(瑜伽行派,Vijñānavāda)那样对意识状态进行层级化结构区分的方式不同,禅宗所强调的是“体用不二”,即本体与作用并非二元对立(见 CBETA,2009d)。
在其著作《禅宗语言研究》(The Language of Chan Buddhism)中,周裕锴(1999)例举了十余种在禅宗中频繁使用的语言形式,涵盖了语言性与非语言性的多种表达方式。其中包括:通过身体动作进行的表达,通过喝斥与击打进行的表达,通过看似无意义的语言进行的表达,通过华丽而又隐晦的语言进行的表达,等等。所有这些表达方式都被认为是在教学互动过程中所采用的善巧手段,其终极目的在于促成觉悟的发生。然而,这种表达策略所承担的风险亦相当之高:一方面,公案禅可能引向某些极端化的实践形式,即所谓的“野狐禅”或“狂禅”;另一方面,禅宗文献本身也往往充满高度象征性且令人困惑的表达方式。胡适与铃木大拙在 20 世纪 50 年代那场著名的论辩中向我们表明,历史研究方法与体验取向的方法各自都能够揭示禅宗的某一侧面。1957 年,铃木大拙与埃里希·弗洛姆(Eric Fromm)等人,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分析系主持了一场以“禅宗与精神分析”为主题的工作坊。这一禅宗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开启了西方学界与大众从心理治疗视角、以及近年从神经科学视角,对禅宗乃至佛教整体持续增长的兴趣浪潮。然而,迄今似乎尚未有研究尝试通过禅宗的解释学原则与心理学原则,对具体公案进行解构,以阐明公案禅那种难以捉摸的内在逻辑。下文中,笔者将尝试结合解释学方法与心理学视角,对禅宗认知、情感、统觉及互动过程中那种跳跃而直觉化的独特运作方式加以诠释。
四、佛教的解释学
不同于《旧约》《新约》与《古兰经》,佛教经典所构成的是一片浩瀚的经典之海——由经藏(Sūtra,佛陀之教导)、律藏(Vinaya,戒律)与论藏(Abhidharma,对佛陀教义的论述)所组成的三藏体系——其形成过程从未像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那样,通过对文献体系进行筛选与审议,从而加以正典化,并明确决定哪些文本应被纳入其神圣经典之中。佛教传统中存在三大佛教正典体系:巴利文正典、汉文正典与藏文正典。其中,作为三者中规模最大的汉文正典(如《乾隆大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若将其全部约一百册(每一册的体量相当于一卷《大英百科全书》)完整译为英文,预计将需要约五十万页的印刷篇幅(Lopez,1988,第 2 页)。在《大正藏》之后,又陆续刊行了汉文佛教的“续藏”,其规模达八十八册,每一册的体量亦与《大正藏》单册相当。面对如此庞大而繁复的经典群体,人们不禁要追问:佛教解释学的核心原则究竟为何?佛教解释学是否也存在类似于 G. B. Madison(1988)所提出的规范性方法,即包含连贯性、全面性、穿透性、彻底性、适切性、语境性等在内的十项解释原则?
在其《佛教解释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Buddhist Hermeneutics)一书中,Donald S. Lopez(1988)对“方便”(upāya,即权宜或善巧方便)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将其视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学原则,或理解佛教文本时所预设的基本前提。Lopez 指出,由于各个佛教宗派普遍坚信佛陀并非不可知论者,如何判定佛陀的究竟立场便成为佛教解释学中的一项核心关切。正因如此,“方便”这一教义本身自然发展为一项重要的解释学原则。他以中国佛教的判教体系,以及上座部佛教中对经典所作的分类体系为例,说明“方便”原则在不同传统中的运用。在众多例证之中,“方便”的典型运用尤为清楚地体现在《法华经》中关于“三乘”的教导:经中以譬喻的方式劝导三类不同的人,分别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从燃烧的房屋中撤离,最终抵达安稳之地。与此类似,我们亦可将公案机锋交流中那种令人惊叹的多样化创造性方法,理解为“方便法门”的具体运用。
Lopez(1988)警告说,若将围绕“方便”(upāya)的解释学关切,仅仅理解为宗派之间的辨术,便会产生误导。他认为,真正促使“方便”原则得以发展的,是对一个更为艰深问题的回应:佛陀最为崇高的见地究竟是什么?佛陀通过其善巧的方法,最终是要引导弟子趋向何种究竟真理?在这一点上,Lopez 与 Robert Buswell(1986)的看法形成呼应,二者共同指出了大乘佛教解释学的根本问题:佛陀觉悟的内容究竟为何?在禅宗语境中,我们可以将这一问题等同为:“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或“心的本性究竟为何?”以及:在心理—灵性层面上,何种描述最为贴近这一状态?而在当代,随着过去二三十年来关于佛教禅修与神经科学的前沿实证研究不断展开,我们还会进一步追问:何种脑波最能表征觉悟状态?觉悟之心所对应的特定神经通路为何?其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MRI)中呈现出怎样的一般性特征?(Austin,1998、2006、2009;Lutz、Dunne 与Davidson,2007)。
除“方便”(upāya)之外,Lopez 还引述了佛陀所教导的四项标准,作为判断其数量庞大且内容多样之教法真义的原则:
依法不依人;
依义不依语;
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依智不依识。
此外,Lopez(1988)援引 Étienne Lamotte 的观点,认为智慧(jñāna)才是真正解释学的决定性工具。Lamotte 将这一立场建立在《解深密经》(Saṃdhinirmocana Sūtra)之上,该经区分了对佛教真理的三种理解阶段:由教法而生的智慧、由思惟而生的智慧,以及由禅修而生的智慧(Lopez,1988,第 7–8 页)。如果我们将最后一种理解视为究竟或决定性的,那么前两种理解方式便只能被视为权宜性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正与佛陀所教“四依”原则中的最后一条——“依智不依识”——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由禅修而生的智慧,正处于禅宗的核心位置。
禅宗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宗派,因此同样遵循“方便”原则以及前述四项判准。尽管如此,禅宗相较而言更为倚重由禅修所生的智慧,并倾向于通过非语言性的表达而非语言表述来呈现这种智慧。祖师禅与默照禅或可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即:由禅修而生的智慧——无论是正式的坐禅修行,还是可能延续至离座之后的持续修行——构成了对佛教真理之理解的一个决定性阶段。而其他类型的禅宗传统,如公案禅与看话禅,则更加强调佛陀教法的最高真理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具体行持中被活现出来(可以推定,其前提是行者已在禅修中体验过这一真理),例如在吃饭、穿衣、洗钵、劈柴等日常活动中,以及在对公案的独立参究与机锋对话的互动过程中。禅宗自称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此禅宗行者——尤其是在公案禅的相遇情境中——常常诉诸于喝斥与棒击,尽管他们同样也会运用柔和之语,而后者正是菩萨道“四摄法”之一。禅宗,尤其是公案禅,频繁运用或以喝斥与棒击作为起始方式的这一特征,使其相较于佛教的一般修行路径,呈现出一种非常规的进路(圣严,1990,第 114–115 页)。因此,对禅宗,尤其是对公案禅的理解,亟需一种禅宗自身的解释学。就其与西方解释学的关联而言,在阐明禅宗与公案相遇之“鲜活经验”的内在逻辑时,可资参照的,是海德格尔(1962)与 Gadamer 所倡导的那种关注前概念与前理解之心灵状态的现象学与哲学解释学传统。
五、禅宗的解释学
5.1 临济宗的原则
禅宗五家各自都发展出一套权宜性的解释原则,用以理解佛陀所教导的最高真理,尽管这些原则在不同宗派之间时有重叠。以临济宗为例,其主要的理解原则体系包括:四料简、四宾主以及四照用(见《五家宗旨纂要》卷上)。
临济宗的四料简,指的是临济禅师在禅宗相遇情境中与弟子或来访者互动的四种方式。其内容包括:(1)破除学人对我的执著,而非对境的执著;(2)破除学人对境的执著,而非对我的执著;(3)同时破除学人对我与境的执着;(4)若学人或来访者对我与境皆无执著,则二者皆不破。至于在具体情境中采用其中某一种,或将数种方式加以结合,其权宜运用完全取决于学人的当下状态或认知取向,以及当时相遇情境的现实条件。
四宾主,字面意为四种“宾—主”或“弟子—师父”的关系形态,是临济宗禅法中的另一项基础性策略。它系统地呈现了在参究禅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四种主(师)与宾(徒)之间的相遇类型:
(1)宾看主,指宾者具备足够的修行经验,能够理解主者;
(2)主看宾,指主者能够洞察、穿透来访宾者的心念;
(3)主看主,指一位主者(或禅师)与另一位主者(或禅师)相遇,双方彼此理解,并处于同一修行频率之中;
(4)宾看宾,指两位宾者之间的相遇,即两位修行者皆“无眼”,尚未具备洞见心之真实本性的能力(星云,1970–1980,第 6506 页;Yuho,1991)。
由此可见,Foulk(2000)所提出的观点——即在公案禅的相遇中,社会层级结构预先决定了师者相对于学人的必然胜出——将会在四宾主之第一、第三种第四种交流与人际互动动态中,遭遇到重要的挑战。
关于临济宗的四照用,至少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版本。在《人天眼目》卷上(CBETA,2009b;T48,第 2006 号)中,“照”字面意为照明、照鉴,被界定为对境的了知;而“用”字面意为运用、作用,则被界定为对自身或主体的了知。其核心旨趣在于教导行者破除将主与客、我与境视为实有实体的分别妄见。正如临济宗“四料简”所示,对主体与客体的执著,皆可通过权宜方便而加以破除。另一种关于四照用的诠释见于《五家宗旨纂要》卷上,其对“照”与“用”的界定则有显著不同。在此版本中,“照”指的是在相遇过程中,于恰当时机展开的语言性交换;而“用”则指在相遇中所采取的非语言性行为,例如喝斥、棒击、面部表情等。《佛光大辞典》卷二对“照”与“用”的运用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
(1)先照后用:禅师先向来访者(学人或宾者)发问,并依据其回答,再诉诸喝斥、棒击等方式加以回应;
(2)先用后照:来访者一入室,禅师便立即以喝斥或棒击相加,随后再追问:“你认为这一切的宗旨何在?”;
(3)照用同时:禅师在喝斥或棒击的同时要求来访者作出回应,甚至可能出现师徒双方相互喝斥或棒击的情形,而禅师仍持续提问,并依据回应加以评断;
(4)照用任运:照与用的运用完全取决于禅师当下的自由裁量(星云,1970–1980,第 677 页;Yuho,1991)。
在《碧岩录》成书的宋代时期,临济宗与云门宗是禅宗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两大宗派(麻天祥,1997;周裕锴,1999)。鉴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主要探讨云门宗的佛教解释学;在适当之处,也将对临济宗的佛教解释学加以参照与讨论。
5.2 云门宗的原则
尽管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临济禅的法系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北宋时期,云门宗却是禅宗五家之中最为流行的一支(麻天祥,1997,第 147 页)。在《碧岩录》所选录的、来自不同法系的一百则公案中,有十四则可直接归属于禅师云门文偃。此外,在圆悟对各则公案所作的篇幅颇为丰富的评唱与解释中,还多次出现对云门的引用与提及,遍布《碧岩录》全书。
要理解云门宗的公案,关键之一在于把握云门三句(即云门的三种根本语句)。这三句分别是:
(1)函盖乾坤句——具有普遍性,能够包容天地万有;
(2)随波逐浪句——善巧地随顺并引导问者当下的处境;
(3)截断众流句——截断问者心中一切分别思惟活动。
然而,三句并非彼此割裂,每一句之中本就内具三句。正因为云门一家的根本宗源本来如此,当云门发出一句话时,此句必当回归其宗源;除此之外的任何理解或运用,终究都只是虚假之说(Cleary 与 Cleary,2005,第 40 页)
云门宗“三中具三、返归宗源”的原则,使人联想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998)所提出的解释学循环:一句话或一部文本的整体意义依赖于其各个部分,而各个部分的意义又反过来依赖于整体。对于这种循环式理解在逻辑上可能引发的缺陷,解释学传统通常通过引入“直觉要素”与“共同理解的领域”来加以化解,从而使解释学循环得以运作(Palmer,1969,第 87 页)。然而,解释学循环与云门三句之间仍存在根本差异:前者主要属于语言学或语法层面的理解结构,而后者则明确指向经验性或心理层面的领悟过程。
在《碧岩录》中,第 6、14、15、27、39、47、50、54、60、62、77、83、86、87则公案都直接涉及云门,或表现为云门与他人之间的教化性问答,或呈现为云门对大众所作的自陈语。圆悟对这十四则云门公案的评唱与阐释中,举出了不少与“截断众流句”高度契合的例子。云门那些在语义层面或社会语言层面上显得不相干的回答,其用意正在于截断问者理性而分别的心念活动。尽管部分禅宗研究者将这种行为模式理解为一种仪式化的实践(Faure,1991;Foulk,2000;McRae,2000,2003),但严格而言,并不存在两则在表达上完全重复的公案。下面以第七十七则、即著名的“云门饼”为例加以说明:
《碧岩录》卷上 · 第七十七则(CBETA,2009a)
【七七】举。
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
云门云:“饼。”
同样地,《碧岩录》第八十三则公案如下:
《碧岩录》卷下,第八十三则(CBETA,2009a)
云门示众云:“古佛与露柱相交,是第几机?”
代众云:“南山云起,北山雨落。”
据圆悟的评唱记载,在云门代众作答之前,曾有一位僧人询问云门:此则公案的教示究竟何在?云门答曰:“一条腰带三十钱。”对于这一在表面上显得与问题毫不相关的回应,圆悟却高度赞叹云门“具鉴别天地之眼”(Cleary 与 Cleary,2005,第 455页)。
那么,云门究竟在说什么?他所做的,无非是截断一切逻辑推理与理性思惟的纷流;而正是这些纷杂的思惟活动,被视为会将修行者引离无分别之境——亦即觉悟。圆悟将这种交流方式称为“无事会”,即一种不以意义关怀为指向、近乎无义却直截的对话形式(2005,第 161、162 页)。
在对第八十三则公案的评唱中,圆悟明确否定了他所认为当时一些人赖以谋生的理性化解读⁽¹²⁾ 。圆悟批评这些解释者“远不知我家宗师之说话,直是截断意识,截断情量,截断生死,截断教中渗漏,直下入正位,更无丝毫留碍。你才拟议思量,便把你手脚捆缚了。”(Cleary 与 Cleary,2005,第 455 页)随后,圆悟又进一步否定了另一种解释取向——“无中唱出”(即“从空无之中发声”)。圆悟否定对第八十三则公案、乃至对公案整体所作的理性化解读,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人不解、甚至颇为困惑的是,他为何同时也否定了“无中唱出”——而这一取向在性质上似乎与圆悟在第二十四则公案中所称许的“无事会”相当。理解二者之间这一可疑差异的关键,在于解释者是否能够“直下入正位,更无丝毫留碍”(李申明、方广昌,1999),亦即是否真正进入一种不滞留任何对象的正确心态。这一状态同时也可被视为海德格尔与伽德马解释学中所强调的前概念的本体论状态。解释者在展开具体的解释学工作之前,必须先退回到这样一种非认知化的状态。由此,人们不禁要问:圆悟,或公案文本本身,是否在暗示一种逻辑——一旦进入了正确的心态,便可以说出相似的话语,却又任意否认其相似的意义?若是如此,这种逻辑是否为纯粹的任意性或不负责任性敞开了大门,而这也正是现象学与哲学解释学屡遭指责之处(Bernstein,1995)?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这是否正是《碧岩录》中多位僧人(例如第十、十九、二十则中的人物)伪装成已觉悟,却最终因其矫饰而遭到喝斥或棒击的原因所在?问题随之转化为:我们应当如何判定,究竟谁具备进行这种“无所关怀式”解释所需的资格、成就与可信度?看似可行的解决方式是:唯有得到普遍承认的觉悟禅师,才有资格对具体的相遇情境或禅宗文本——尤其是其中具有争议性的部分——作出恰当的解释。这一点本身即构成了禅宗解释学的一项原则(Chappell,1988,第 193 页,转引自 Lopez,1988;Faure,1991)。而从结构层面来看,Foulk(2000)则将这一现象归因于社会等级结构。
那么,如果禅师的解释本身出现偏差,又当如何理解?我们或可设想以下四种可能的结果:
(1)如 Gadamer(2004)在其对人类知觉与认知的讨论中所尝试的那样,将这种偏差视为一种“赋能性的偏见”(enabling bias),从而为其正当化
(2)某些误解或误读,可能在具体语境中比其他解读更接近文本的真实意涵,或者说,它们“通过其生成性的成果而获得验证”(Faure,1993,第 138 页);
(3)解释与言说的自由运作并非没有代价;依照佛教的因果业报理论,这种代价将转化为行动者自身所承受的相应业果报应(Faure,1993,第 138 页);
(4)McRae 所提出的禅宗研究第一定律:它并不真实,因此反而更加重要(2003,第 6 页)。
McRae 在此所指的,是禅宗历史事件在事实层面上的不确定性,相较之下,“传说与神话如何在大众意识中存活”反而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2000,第 74 页)。
鉴于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已显露出诸多显著问题(Faure,1993,第 110–113 页;Gadamer,2004),McRae 或许有必要至少指认一种替代性的研究取向——相对于对历史现实的诉求,转而指向心理层面或超个人层面:即那种前概念的、无分别的、无所关怀的禅宗心态。尽管这一心态本身具有瞬时性(围绕这一心态所形成的发展阶段则相对稳定),但它在心理学意义上与存在论意义上都是真实且成立的。
在考察了云门“截断众流”之语后,下面转而来看另一类“随波逐浪”的示教方式。在圆悟对《碧岩录》第三十九则公案的评唱中,嵌入了另一则云门公案,其内容如下:
《碧岩录》卷上,第三十九则(CBETA,2009a)
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
云门云:“清波无透路。”
僧云:“和尚作么生?”
云门云:“这第二问从甚么处来?”
僧云:“恁么去时如何?”
云门云:“转多途路塞。”
【英译对应文本的中文直译】
一名僧人问云门:“佛法是否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
云门回答:“清澈的波浪中,没有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
那名僧人继续问:“那么和尚你是如何行的呢?”
云门说:“你这第二个问题,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僧人又问:“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会是怎样?”
云门回答:“越是转向多种途径,路反而被堵死了。”
(Cleary & Cleary, 2005, pp. 241–242)
当云门以“清波无透路”作答时,似乎意在当即阻断问者的理性思惟。僧人继续追问之际,云门又通过反问“这第二问从甚么处来?”,再次尝试引导问者去亲证空性,或以海德格尔—Gadamer 之说,进入一种前概念的认知状态。当云门意识到来访僧人未能领会其意时,便暂时退却,转而采取另一条路径,给出较为可理解、也更为常规的说明;他下移一步,以贴近一般问者的层级,单纯顺着对方的思路与频率而行。
在圆悟对《碧岩录》第三十三则公案的评唱中,云门与陈操的相遇,更清楚地体现了这种“随波逐浪”的示教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陈操的身份有关——他既是居士,又是新儒学(理学)学者。其公案如下:
《碧岩录》卷上,第三十三则(CBETA,2009a)
一日云门到。陈操见,便问:“儒书不问,三乘十二分教各有教授。衲僧行脚意旨如何?”
云门云:“你问多少人来?”
操云:“只今问和尚。”
云门云:“且置‘只今’,教意作么生?”
操云:“黄卷赤轴。”
云门云:“这是文字言句,教意作么生?”
操云:“口欲言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
云门云:“‘口欲言而辞丧’,是存言;‘心欲缘而虑亡’,是妄想。教意作么生?”
……
操无语。
【 (Cleary & Cleary, 2005, p. 207)直译中文】
有一天,云门来到此处;陈操一见到他,立刻问道:“我不问儒家经典中所说的内容;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其各自的讲解者。那么,一个身披补衲、徒步行脚的出家人,究竟是为了什么?”
云门说道:“你已经问过多少人了?”
陈操说:“我现在正是在问你。”
云门说道:“暂且把‘现在’放在一边不谈,那么,教法的意义是什么?”
陈操说:“黄卷朱轴。”
云门说道:“这些只是文字与书写;那么,教法的意义是什么?”
陈操说:“当口欲言说时,言语便逃逸;当心欲与之相应时,念头便消失。
云门说道:“‘当口欲言说时,言语便逃逸’,这是指执着于语言;‘当心欲与之相应时,念头便消失’,这是指落入虚妄的概念作用。那么,教法的意义是什么?”
……
陈操无言。
我认为,云门的“截断众流句”与“随波逐浪句”,分别对应于由云门弟子洞山所开创的两种公案参究方法。这两种方法即是:参活句与参死句。在这一传统中,那些在理性层面上看似富有意义、可供理解与分析的语句,反而被称为“死句”,因为它们“只能澄清理解,却永远无法带来真实的证悟”(Buswell,1986,第 221 页)。参死句的方式,似乎可与云门的“随波逐浪句”相对应:它从学习者当下所处的位置出发,引导其向前推进,却并不直接指向究竟真理。相对而言,那些对于理性理解而言显得“无味”、不相干,甚至荒诞无义的语句,则被称为“活句”,因为它们不允许任何概念性的理解介入,也不给迷妄之心留下任何可执取之处。因此,参活句的方式,显然与云门的“截断众流句”相互呼应;在学习者机缘相应的情况下,这种方式表现为明确、骤然且具有穿透力的示教。若以瑜伽行派/唯识学(Yogācāra 或 Vijñānavāda)理论作为一种解释学工具,我们便能够进一步解读:参活句之所以得以发挥作用,是通过八识转化这一心理—意识结构的根本变革而实现的(朱彩方,2005)。
云门亦常以单字或单句作为示教之法。有人问:“杀父杀母,向佛忏悔;杀佛杀祖,向谁忏悔?”云门答曰:“露。”又有人问:“什么是正眼法藏?”云门答曰:“普。”(Cleary 与 Cleary,2005,第 39 页)。这些回答亦可被理解为云门对另一类语句的运用,即“函盖乾坤句”。此类语句往往高度抽象,似乎主要在哲学或神秘层面上具有指涉意义。它们或许听来晦涩、隐秘,然而,这种表达方式或许可由更高层次的原则加以正当化:其一是“一句之中具三句”的原则;其二则是更为根本的原则——“万象千形,一切言说,皆须回转向己,令其自转自在”(Cleary 与 Cleary,2005,第 40、94、241页)。
圆悟所说“一切皆须回转向己,并令其自在运转”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解释认为,这一原则超越了禅宗五家在风格上的差异,因此可被视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原则,普遍适用于各宗各派。另一种解释,则将我们直接引向海德格尔与 Gadamer 的解释学传统: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如何必须首先回溯并反映到对“存在本身”及其本体论存在状态的理解之上?认知之心是如何运作的?而这种认知过程,又如何影响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Chappell,1988;Gadamer,2004;Husserl,1970;Palmer,1969)。既然一切都应当回转向己,并被赋予自在运转的可能,那么,在双向相遇的情境中,承担主动角色的并不仅是禅宗行者,同样也是文本的解释者;二者皆需主动使一切得以自在运转。由此引出的关键问题在于:禅师是在何时、又是如何使情境发生自在转化的?这一问题必然引出“禅机”这一主题——即转变发生的契机或恰当时刻;而这正是公案禅解释学中的核心要素。
 中文版
中文版 English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