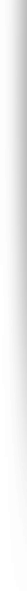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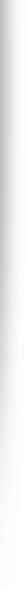
药山寺.竹林禅院后记 – 禅院五日,得小自在
汪子君
来到大殿处,才发现我们来早了,只有两位师兄在殿内做准备。一位师兄微笑着示意我可以帮忙插香,她说:插直就可以了。我来到最正中的佛香前,小心翼翼地,将三根点好的香插进去,没成想第一次竟歪得不成样子,又试了一次,仍然不直。我感叹: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呀...师兄在旁边关照,笑说:“是吧,每件事,无论再小,都是修行。”第三次,我尝试着静下来,听着自己略微紧促的呼吸声,感受着脑袋中杂念的此起彼伏,看着自己双手不自然且僵直的动作,慢慢地完成了一次勉强过得去的插香。
不一会儿,所有师兄们都陆陆续续地进殿了,早课开始。到了唱诵环节,我们几位新来者有时找不着经文页面,有时又不认识其中一些字,但还是努力地去认真跟随。后来站的久了,加上早上起得太早,我开始觉得晕晕乎乎的,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但面对这样神圣的仪式,又觉不宜分心,便反复用正念提醒自己回到当下,只做正在做的。
结束后才6:10,天是蒙蒙亮的,一行人来到斋堂。早粥开始之前,要念“供养偈”和“结斋偈”,念完拜佛,礼毕,待师父们取完餐后,我们才会去排队取食。吃饭的时候就只是吃饭,不聊天不看手机,不东张西望,也不三心二意。这样的正念吃饭让我的肠胃通顺了很多,身体也更舒畅了。虽然我每天吃饭时都要过目一遍桌面上的“食存五观”,里头有句话说:对所受的食物,美味的不起贪念,中味的不起痴心,下等的不起瞋心。但我还是想说这么一句有分别心的话:竹林禅院的斋堂自助餐太可口了!让我体味到了湘菜的本真,简直比我吃过的所有斋饭(甚至是绝大部分餐食)都要好吃。它令我至今回味无穷。听师兄说掌管斋堂的小伙子是位00后,之前在长沙做素食。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看起来年轻有活力,却有着一般这个年纪没有的某种自在自若,也总是笑着,一身轻松。
这天下午,明影法师的心经导读和晚饭后的行禅、坐禅也让我受益匪浅。我听读过心经多遍,在法师讲解之后,才更知其真意、珍贵。法师的很多阐述看似平淡如常,但他对每个字每段经文都有着抽丝剥茧的探索和切身的感知体悟。比如他说“心念的变化最无常,我们要以观心观无常”,而在无常的变化幻象之中,“一切法无得无失,何不由对波浪的追逐,转为与水相契合”。这里,“水”代表五蕴的“空”,而波浪,则是一切变化的表象,即幻象、无相。诸佛智慧,是既能“观自在”,也就是安住自在本体,又能“照见五蕴皆空”的。法师的讲坛让我感觉到读经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更是一种极其精微深远的修行。经文里的每个字每个词都不是头脑层面的知识或语言学文本,它们是一粒又一粒珍珠,永远晶莹剔透地显化出白玉光,而我们眼中所看到的,更多只是紧闭着的贝壳,要想打开来见真珠,是要下功夫的。其实,贝壳它自己会张嘴吐珠的,我们要有智慧去参悟。
晚上的行香坐禅与我们平日里练的有所不同,比如说行禅是快速的,男众女众是分开的...坐禅时,只留佛和光在中间。一关灯,幻象似乎也全灭了;一闭眼,佛和光自然在心间。那一瞬间,我的眼眶突然湿润。但很快,我明显地感受到,这莫名的悲伤,被在场的佛、师父师兄们托住了,它不会因依附而溢出、不因抗拒而被抑制。这份悲伤只是来了,又流走了,这个过程是自然的平常的,跟平时我处理悲伤的惯性反应完全不一样。它是一种只当下关照的“不处理”。后来当我回味这一刹那时,又再次感受到了内在那永恒的、本来存在的流动,也看见师父师兄们亦是佛。那我自己呢?不也是其中一员吗?我也承接了自己的心呀。
第二日在明影法师《六祖坛经》导读时,提到“菩提自性"、“自心本具佛性”时,联想到坐禅时的体验,便更觉体悟了,也更相信自己能够担当了 – 无论是起心动念、喜怒哀乐,还是日常中感受到行动着的一切。
短短一日,我感知到处处有佛,事事皆修行,从最日常的吃穿住行、看听感闻、言语行动到规律化的学习和练习,每一个当下都在提醒我们:修行就是平常的生活本身。
今天明影法师《六祖坛经》的导读和公案分享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到了“心”。法师说“见本心,见自性佛”。但是,“我们的心常常是黑黢黢的,更不知道妄想何起。”我对此深有体会,尤其在当天晚上坐禅时,一闭上眼睛,确实能感受到心是一片黑黢黢的,有时妄念多的堵塞了通道,没有一丝缝隙能够让光透进来,甚至找不到心的位置;有时只感到一片混沌,不知所向。这一次的静坐,我没有用任何学过的正念技巧,也没有任何预设或期待,我只是坐在这里,静静地观。但是,尽管面对的是这黑黢黢的心,我也没有丝毫恐惧。我想,一是因为白天法师讲这一段时,说的是绝大部分人,我感觉到自己并非不正常也并不孤单;二是我感受到自己如此赤裸地完全敞开,不留一丝余地,反而很释然了,不管看到的是黑暗还是一丝丝光亮,都是对自己内在状态的如是承认。
每晚的行香坐禅后,我们的安通小组按惯例开始了线上下打通的读书会。能够来到线下的人都很庆幸很喜悦,并且与没法来到的同学们约定着下次再来,可见禅院的吸引力非同凡响。而且在远离尘世的地方相见,每个人都极其珍惜这静心实修、学佛明心的绝好机会。
清晨天未亮,在梦里醒来,身心像是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缠绕的重物,我知它是积业,亦是存在本身的沉甸甸。突然,一声晨钟敲破了静寂,在空气中蔓延开来。一声又一声,响在我的耳边,也敲打着我的灵魂。我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仿佛无力僵硬的身体被钟声晃动了起来,胸口也被做着心肺复苏,这一刻,我感知到了这个生命体,也就活过来了,因此泪流满面。这偌大的空无的天地之间,没有我,没有床铺,没有房间,没有遮盖,只有钟声,只有生命,无边无际,无苦集灭道。我想,是潜意识里深藏的一些创伤在静谧的寺院生活和学修中冒出头来,经由巨大能量体的晨钟,我得到了一些释放。
而当晚在明影禅师专门给安通学员的问答中,我也找到了可能的转化之道。他说:“任何的想法和心结,都可以当作此时此刻的参禅、修行。要依据佛法智慧,发菩提心,解构妄念后,再去建构真相。人总会有思想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总会时不时回到小我的欲望里,要大量的学习,在无数的熏陶和实践中读懂、消化、重建价值观;而当这些矛盾反应在每个人的身心、生活、关系和家庭时,只能持续地去修行,去看见它们的真实面目,而后去担当责任,这就是生活禅。”一切烦恼和伤痛,都是菩提,都是来提醒我要回到自身的基础修行,允许自我意识、行为习惯、思维人格和情绪情感去穿越层层黑暗,去从混沌无明之中跳出来,去勇敢地承担起这复杂的生命改造过程,很多人无法担当,是因为他不想面对其中的痛苦和困难。宁愿痛苦,也不愿改变,这样只会召集更多的苦,由苦到集再到苦。如果我想要经由苦集到灭道,让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受益,就需要带着障碍走下去,去扎扎实实的面对和担当。“对烦恼要有耐心,因为烦恼是自己的,是自己以前造作起来的,那就得去担当起来。”法师在白天的生活禅修讲座中亦如是说。
问答中法师还提到了开悟的人行住坐卧、言行举止皆明心见性,而没有开悟之前,还是要体验,要静下来。“禅坐不是为了禅定,而是为了般若智慧的深化。一切为打坐服务,仅仅打坐绝对不够,没有打坐绝对不行。”另外,关于坐禅时瞌睡而进入催眠态,他说,这对当代人来说只起到了休息减压的作用,并不能进化智慧。对于冥想时的思维,要追求“不思之思”:思维我们的本性,思维我们的不思维。因为思维是智慧的工具,所以它需要活跃,但同时,不能让它落入分别心和评判。这些都很好地解答了关于我在冥想静坐时的种种困惑,法师在答疑解惑时,总是能异常精准的切中底层的本质和真相,并且在解构和建构之间游刃有余,来去自如,我想,这就是修练出来的般若智慧中的超越局限的自由状态吧,即便是在一言一语中,也处处能彰显。
之所以把第四日和第五日放在一起写,是因为第四日的学习内容主要是《禅修疗法》,实修照常。而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文章已经单独写了,就不再放于此处。在禅院的第四天,我已经非常习惯这儿的吃穿住行和日常学修了,心里边竟觉得熟悉无比,像是回到了真正想要的家,十分安心、从容。正如我在最后一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样,现在回过头看,似乎从小到大跟佛的缘分就没有断过,从小时候和青少年期经常跟家人朋友去旁边的寺庙景点走走,到大学毕业后去了柬埔寨两年,作为佛教国家,它无时不刻地在社交、文化交流和玩乐旅游中向我呈现佛教的历史、建筑,以及深入日常生活的“佛系”:纯粹、简单、快乐、无忧无虑、不急不躁,你可以在每一位平民大众的脸上,看见吴哥的微笑。后来在美国读硕士时,遇到了宗教系一位自称“内黄外白”的诗人导师,他研究藏传佛教,让我读英文版的佛经,还经常鼓励我多写自己语言的文字。不过这些都只是种下的种子,在那些当下,佛教在我的认知里是宗教的一种,以及某种神秘的力量,我并没有主动地去深入研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我一直有去正念中心和禅修中心冥想的习惯,但也很少去探索冥想的来处。
直到命运让我从西方回到了东方,因缘际会遇见了朱彩方老师,听了他的很多讲学音频,上了安通疗法的课程,来到了禅院,我才真正有所实修和体悟,每每都会惊觉:佛学真的是大智慧!它不只是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更是既普世又出世的心灵指引,它既简单直入又错综复杂,既存在于当下的一呼一吸之间,又似乎是高不可攀的深奥、远不可及的开悟。我觉得它应该纳入九年义务教育之中,每个人都应该从小时候开始,就去体验这将受益一生乃至生生世世的般若智慧。可惜咱们的意识形态还没有进步到如此境界,反倒西方人士捷足先登,取了一些浅表的技巧去进行商业化的正念推广。我们在最后一日的清晨,相约去旁边的竹林和山野散步。11月深秋的晨光,是易碎的玻璃质感,如人类的心灵,需要在一呼一吸间,小心呵护;但同时,它们都是不可知不可见的无限能量,于无形无声之中,穿透一切又容纳一切。我们从光中来,同时循光而去;在旷野里,每一株沾满露水的草,每一朵生长中的花,都与我们同在,也便没有了‘我’,没有了‘他’。
结束便是开始
离开禅院要回到尘世的路上,我就生发了不舍及我执之相,脑袋里想着:“唉,又要回到混沌生活之中了。”又无明的思考着:怎么才能一直过上像这几日的生活呢?心安心静,一无所求。出家修行吗?好像尘世间放不下、未完成的还有很多很多...我观察着自己的杂念,倒也觉得有趣,也许自己还是有许多牵扯,要一遍又一遍地回去体验、看见、静观,要反反复复的一点一点的练习放下。再说了,世间生活本来就是修行呀!后来我追问一位短暂出家一年的朋友,问他当初是什么让他下定决心,又是什么让他返回世间。他说这不是脑袋想出来的,也没有任何计划,当时他就一心想要,别无它念,觉得时机已到,出家就出家了。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也经历了从欣喜到煎熬再到适应和平常心的种种阶段。最后又选择回来尘世,也是因为内在感到有很多人事未尽,回来也就回来了,顺其自然,并不纠结。是呀,这本就不是头脑和意念能做主的事儿,随它来也由他去吧!
再后来,隔了不久,当我在明向文化筹办的Lattuada博士生命能量转化工作坊中,体验与大师同行的登顶萨满“回家”之旅时,我的灵视似乎就是在禅院湖边的那条路上,有多位大师与我同行,但到结束时,得由我一人前行,我不知所向,踌躇不前,不知道怎么回家了。当我跟朱老师分享这一感受时,他只蜻蜓点水般,微笑着说:“那就随便走,哪里都是路,都可以回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是呀,从禅院和大师那儿获得很多指引,也得到内在的些许体悟之后,无论走哪一条道,无论迷惑不已还是障碍不断,只管行走就是了,只管打坐就是了,都能回到家中。而且当下此刻,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家中”。
END
如想报名2024年6月1-2日竹林禅院超个人修学之旅,请点击详情:竹林禅院 || 超个人心理学修学之旅招募
(*目前只剩非在读生的社会名额一两位,对超个人心理学和禅修的研究深造感兴趣者*)
 中文版
中文版 English
English

